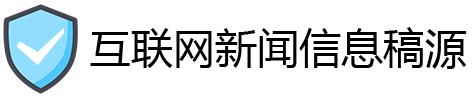火塘·鄉(xiāng)愁 余光龍 攝
傅海清
關于火塘的記憶,總在某個不經(jīng)意的瞬間悄然浮現(xiàn)。無論走多遠,鳳凰縣老家那棟木房子,還有鄰村岳父母家木屋里,那方嵌在堂屋中央或偏房的火塘,連同圍坐的人、說過的話、升騰的煙火,都深深烙印在腦海里,揮之不去。
當年我家蓋木房的場景,至今清晰如昨。建房的屋柱、橫梁是從自家坡上砍的,唯獨主梁是按老規(guī)矩“偷”的——這不是真的偷東西,而是鄰里間心照不宣的習俗,老輩們說這樣日子才能興旺。村里的木匠寶叔是建房高手,他手中的墨斗線一彈,筆直的印子便刻在木頭上;斧子一上一下,木屑飛濺,刨子推過,原木上細膩的紋絡就露了出來。那些鑿好榫卯的木構件,凹的地方對著凸的地方,嚴絲合縫地拼在一起。幾十個人拽著粗繩子,喊著號子,笨重的木架便穩(wěn)穩(wěn)立了起來,經(jīng)得住大山的風吹雨打。寶叔把“偷”來的梁木架在堂屋臨時木架上,嘴里念叨著吉祥話,用斧子在梁木中間刨出細槽。父親趕緊舉著竹篩在底下接,說是“財氣不掉”。接著,父親遞過幾枚硬幣,寶叔一一塞進槽縫,再用紅布仔細裹緊。屋頂早有兩個年輕人搭了木梯爬上去,放下繩子。下面的人將繩子捆住梁木兩頭,寶叔邊爬梯子邊唱上梁詞,鞭炮聲一響,梁木緩緩歸位。大哥二哥緊跟著爬上去,坐在梁的兩端,從竹籃里往下扔糍粑——院子里的人有的舉著衣襟接,有的端著簸箕接,有時糍粑掉在地上,大家搶得不亦樂乎。
房架立好后,砌墻用的土磚得自己動手做。父親那段時間一直在田里忙碌,牽著牛把泥地踩得均勻又結(jié)實。等泥巴不軟不硬時,父親便拿出一個木框子,然后用鐵耙鏟起泥巴往里面填,填得滿滿的,再用木板把泥巴壓實,輕輕抽出木框,一塊方方正正的泥坯就做成了。如此反復做,泥坯曬干變硬便是土磚。這些帶著泥土味道的土磚,將房子圍得嚴嚴實實的,冬天住在里面,比磚石房還暖和。
溫暖而清晰的還有那些與火塘相關的往事。火塘是父親在堂屋中央挖的四方土坑,周圍用石頭壘得牢牢的。他總說:“火塘是四四方方一丘田,天天在家里走冒(不)遠。”這“田”的用處可多了:天冷了,燒起柴火,一家人圍坐著烤手;臘月里,火塘上方掛起臘肉、豆腐,煙火慢慢熏烤著,香味飄得老遠;餓了,火塘邊烤糍粑再方便不過了,不一會兒糍粑就烤得脹鼓鼓的,既好看又好吃。當然,平時在火塘上架上一口鐵鍋煮飯炒菜,或往火邊放個紅薯,都是再實在不過的美味。火塘邊偶爾煙多,我們小孩不想被煙嗆到,就學著父母教的童謠念:“煙子煙,莫煙我,我是天上梅花朵,豬劈柴,狗燒火,貓兒洗臉笑死我。”逗得大人們發(fā)笑。
火塘邊有難忘的故事會。夜晚,忙碌一天的奶奶,喜歡在火塘邊煨一鍋稀湯,任火苗照著她臉上的皺紋,然后不緊不慢地給我們講“熊外婆”的故事。我們幾個小孩聽得又愛又怕,眼睛緊盯著奶奶,生怕錯過任何一個情節(jié)。父親則愛在火塘邊給我們出謎語,或講“兩弟兄分家”的故事,教育我們要團結(jié)、謙讓。
那時火塘就是家的“中心”。大人們圍坐著說莊稼的長勢,講村里的新鮮事;小孩要么趴在小板凳上寫作業(yè),要么在旁邊玩紙板,要么用棉線挑出各種花樣。家里來了客人,也不用特意收拾,大家圍著火塘而坐,把自家的草煙絲遞來遞去,說的都是心里話。
大年三十晚上,還有在火塘“燒旺火”的習俗。木柴在火塘里“畢畢剝剝”地燃燒,一家人圍著火塘包餃子,其樂融融。就算日子再難,父母也會給我們幾個發(fā)壓歲錢,錢不多,但收到心里暖暖的。后來,三哥買了一臺黑白電視機,過年時一家人便圍坐在火塘邊收看中央電視臺的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那份暖和而愜意的滋味,至今回想起來仍覺得舒心。
結(jié)婚后,我經(jīng)常陪妻子回岳父家。岳父家也是木房子,只是火塘設在客廳旁邊的小屋里。岳父是老黨員、老村支書,總愛坐在火塘邊,守著那臺24英寸的黑白電視看新聞和革命戰(zhàn)斗片。就是在這火塘邊,他把一塊手表遞給我,說:“這塊表送給你,看著時間做事方便些。”那份沉甸甸的心意,到現(xiàn)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可惜的是,后來,木房子拆了,蓋起了水泥磚樓房。前幾年,岳父和岳母永遠地離開了……
我的父親走得比岳父母還早。母親跟著在外地打工的哥嫂幫忙帶孩子,沒人打理老家的木房子,它便在風吹雨打中慢慢塌了,那方火塘,也被雜物埋了起來。再后來,二哥在原址上蓋起了樓房,冬天取暖,要么用火盆,要么開電爐,確實干凈多了,但總覺得少了點什么。
現(xiàn)在我們住在鳳凰縣城里,冷了就開空調(diào),偶爾打開75英寸的彩色電視,卻再也沒見過火塘。可我總想起父親挖的那方火塘,想起火塘上的縷縷煙火和糍粑香,想起奶奶講的故事、父親出的謎語,還有岳父遞來手表時的模樣,以及大年三十晚上火塘邊的歡聲笑語。那些火塘邊的日子,那些歲月里的親情陪伴,一直溫暖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