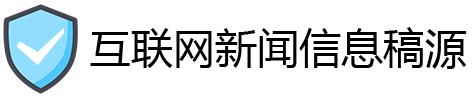潕溪書院內有百年老藤。“藤翁”二字由黃永玉題寫。 團結報全媒體記者 石健 攝
團結報全媒體記者 吳剛
1
不怕人笑話,我其實挺自卑的。
也許是由于小時候物質條件十分艱苦的緣故,也許是出于生長在湘西“小地方”的緣故,也許是因為地域或民族普遍心理都比較敏感的緣故,長期以來,我從未覺得,在我的身上以及在我的身邊,有何可以牛皮哄哄的理由。
少年時,我曾經暗自羨慕那些有條件玩航模、聽音樂會、騎單車上學的大城市同齡人;青年時,我自覺不自覺地跟著外地風潮學下圍棋、跳霹靂舞、寫朦朧詩、唱粵語歌——不吹牛,1995年以前發行的粵語歌,我至少會唱95%。
我不知道,在我的湘西家鄉,有多少人和我一樣——有過于強烈的地域“自豪感”。
年輕漂泊外鄉時,有人嘲笑我是湘西土匪,我把他“捶”了一餐;有人問我吃不吃生肉,我把他“捶”了一餐;還有個湘西老鄉對外謊稱他是懷化人,知道我是吉首人后,又來套近乎跟我講他是隔壁縣的,我同樣把他“捶”了一餐……
不可碰觸的深刻自卑。
2
我的自卑,還真不光因為物質條件,主要還是文化上的。
我雖然非常喜歡我的家鄉峒河峽谷:兩岸懸崖兀兀,崖下深林莽莽,林下煙村裊裊,村外稻浪田田,田邊河水澹澹,河畔筒車悠悠,有藍天,有白云,有雞鴨蟬嘶叫,有鷺鷥飛過……我覺得很美,但是對比掛歷里的大城市,長街繁榮、大廈林立、名樓顯赫、學府莊嚴、衣裝時尚,那股“我家鄉也很牛”的忐忑的膨脹感,瞬間漏氣。甚至,當年那種男的坐在草地上彈吉他、女的擺Pose的掛歷畫,都讓我覺得,那是比我高級的、有文化的生活。
即便在狹義文化的領域——我很努力地去學習那些我自認為“很有文化”的雅事,卻不得不面對“一個人玩”的困境——我的周圍,沒人和我談格律詩的平仄拗救,沒人和我談柏拉圖的國家試驗,沒人和我談《金枝》的巫術原理,更沒有人和我談王東岳的“遞弱代償”……倘若我硬要在朋友們“炸口水”的時候強行插入此類話題,必然收獲“酸不溜秋”的中肯評價,止增笑耳。
以至于我常常在想,也許我也可以跟大家一樣,在“文化不自信”上躺平擺爛,反而能獲得“我沒文化我怕誰”的另類優越感,再去嘲笑他人。
3
但后來,后來,后來……隨著信息扁平化時代的到來,隨著對外界、對湘西的認知日深,隨著文化比較變得更加容易,我覺得我又行了——哦不,我的湘西又行了。
我的湘西,是地球演變史的重要記錄地,兩顆“金釘子”(全球年代地層單位界線層型剖面和點位),漫山遍野的三葉蟲化石,見證了寒武紀生命大爆發的壯闊奇跡;我的湘西,是第四紀冰川中的綠色氣孔,荒野里肆意生長的杜仲、水杉、珙桐、獼猴桃,炫耀著孑遺物種藏身生命避難所的絕世好運;我的湘西,矮寨大橋一帶,是全球峽谷最密集的地區,沒有之一。
三萬九千年前,舊石器時代的先民,就在湘西的藥王洞里點燃篝火,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危險的夜晚;四千八百年前,新石器時代的先民,就在湘西的沅水岸邊砌土為窯,燒制了一件又一件精美的陶罐。
在我的湘西,流傳著伏羲女媧兄妹成婚的傳說,隱藏著史前大洪水的明確記憶;在我的湘西,講述著盤弧辛女教化山民的故事,旁證了三皇五帝不遺余力傳播文明。
后來,屈原來到我的湘西,對天哭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后來,秦人來到我的湘西,把乘法口訣表,埋進了里耶古井;后來,王陽明來到我的湘西,開壇授課,知行合一。
后來,王陽明的學生吳鶴,在吉首的峒河邊,創辦了一座“潕溪書院”,至今已傳承了512年。
原來,五百年前,我們的湘西,就有了書院——和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東林書院一樣的正經書院,有人像梁山伯祝英臺一樣穿古裝搖頭晃腦讀書的那種真正的古代書院。
原來,我的湘西,祖上很“闊”。
4
更不用說,我的湘西,生活著浪漫堅韌的土家族和苗族,他們創造了絢麗多彩的文化,全部具有中華文明意境含蓄、意向飛揚的典型審美。
我的湘西,以異質的自然風光和異質的民族風情著稱于世,擁有1座世界地質公園、2個國家5A級景區,還擁有1項世界文化遺產、1項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28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多達278項的州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神秘湘西”天下馳名。
試問,世界上,又有幾個地方,敢號稱“神秘”卻又無人反駁?
憑的就是我們擁有足夠獨特、足夠多元、足夠精彩的文化家底。
憑的就是我們的文化,見證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融合、發展的全過程,雄辯地證明了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的總特征。
憑的就是我們的文化,凝聚了各族人民共同交往生活的記憶、感知與期許,緊密地筑成了認可認同、相依相存、共信共進的民族共同體意識。
就憑這一手沉甸甸的文化,我們湘西,該不該自豪,該不該自信?
4月10日,人間春好,“湘西州政協文史教育基地”在潕溪書院掛牌;同日,“湘西文史講堂”在吉首大學師范學院大禮堂首場開講,題目是《詩篇還為故人留——王陽明與永順土司淵源及影響》,座無虛席。
一縷致力于喚醒湘西文化自信的勁風,于斯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