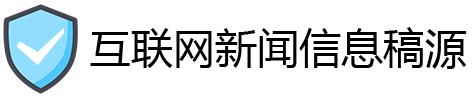田凱頻
1966年冬天,艾黎先生來鳳凰,已經(jīng)是“改天換地”后的新面目了。盡管如此,他仍然覺得鳳凰很美,認(rèn)為鳳凰和長(zhǎng)汀是“中國(guó)最美的兩個(gè)小城”。
艾黎并不是最先來鳳凰的洋人。早在1926年,加拿大的甘教士和美國(guó)的達(dá)教士來鳳凰傳教,創(chuàng)建福音堂,在鳳凰生活了六年。1929年,美國(guó)神甫楊夢(mèng)齡來鳳凰創(chuàng)建天主教堂,之后洪神甫、費(fèi)神甫等三人先后來到鳳凰,管理教堂。那個(gè)年代里,他們應(yīng)該領(lǐng)略到鳳凰小城的美,山水的美,人民的美,文化的美,但沒留下文獻(xiàn)記載。
原本的鳳凰城,四周環(huán)圍的城垣,鉚厚鐵皮的城門,石板鋪成的街道,寬窄錯(cuò)落的巷弄,依地勢(shì)建筑的民居,整修規(guī)矩的長(zhǎng)石條豎嵌入河底的石槽里架起的跳巖,半懸在河邊用木柱支撐的吊腳樓,河邊的磚塔,城中的寺廟,各姓的宗祠,有錢人家的大宅院,連同官禁山、奇峰寺、文昌閣的很多大樹,都是古老的。城里的居民和進(jìn)城的鄉(xiāng)民一樣皆是淳樸的,他們依著一直的習(xí)慣和固有的分定過著平常的日子。這樣的格局,對(duì)所有漂洋過海的洋人來說,自然有著強(qiáng)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端午節(jié)后,來鳳凰的洋人多了起來。男女老少,單獨(dú)的,成群的,花花綠綠,斷不清來自哪些國(guó)家。鳳凰人和許多地方人一樣,把外國(guó)人統(tǒng)稱作“洋人”。
洋人與我們有很多不同,除了膚色相貌,他們背著行囊,挎著相機(jī),不打太陽傘,不穿防曬服,不戴防曬面罩和臂套,至多戴副寬大的墨鏡。他們大都不喜歡扎堆,不喜歡在人多的地方添堵,也不請(qǐng)導(dǎo)游,似乎更相信自己的眼睛。走在古老的石板街上,或是沿著殘缺的城墻根腳,或是大院高墻下的窄弄里。祠堂的戲臺(tái),跳巖的石墩,虹橋的石拱,廟宇的塑像,城門的鐵釘,古宅的鰲頭,灰墻的花案,門窗的雕花,蠟染的印版,中國(guó)的旗袍,苗族的銀飾……不聲不響,細(xì)細(xì)地看,慢慢地拍,拿著小本子寫寫畫畫。大概他們是在現(xiàn)代生活的小城里,各處尋找沈從文先生過去的印象。到了飯點(diǎn),撿一家小飯館點(diǎn)一兩個(gè)菜,吃得干干凈凈。走得累了,尋一家咖啡館坐下,點(diǎn)一杯咖啡,安靜優(yōu)雅地喝。吃過喝完繼續(xù)走,繼續(xù)看,繼續(xù)拍,繼續(xù)寫寫畫畫。大多國(guó)內(nèi)游客,特別是青年男女,來到鳳凰,只熱衷過跳巖的刺激,坐游船的愜意,看吊腳樓的奇巧,看燈光秀的斑斕,然后漢服唐服苗服化妝拍照,在銀器店姜糖店燒烤店里合理地分配囊中的鈔票。
前幾天,路過南華里,看到幾個(gè)年輕的洋人坐在“1892”咖啡館外廊上喝咖啡,悠然自得,輕松自在。聯(lián)想到沈從文、艾黎、黃永玉、金介甫等把鳳凰推向世界的文化名人,突然萌生拍一組外國(guó)人在鳳凰的片子的想法。取出相機(jī),換上200的鏡頭,站在遠(yuǎn)處拍了幾張,片子出來,感覺有半人文半沙龍的味道。
接下來幾天,挎著相機(jī),在古城里轉(zhuǎn)悠,捕捉需要的人物與場(chǎng)面。
走出廣場(chǎng),回頭看見兩個(gè)洋人,一個(gè)帥小伙,一個(gè)稍大一點(diǎn)的女士,坐在鑄鐵欄桿下的條凳上休息。小伙子在看鳳凰旅游圖,女士手持咖啡,慢慢喝著,樣子很悠閑。我老遠(yuǎn)站在田君健故居門口,用墻體作掩護(hù),試著連拍幾張。女士發(fā)現(xiàn)我鏡頭對(duì)著他們,先是一笑。我連忙指著手里的相機(jī),指指他們,意思是“我在拍你們”。女士很大方,做了“OK” 手形,然后我們都笑了。
在道門口轉(zhuǎn)了幾圈,又碰上他們,友好地打了招呼。帥小伙用中文對(duì)我說:“您好!我可以加你微信嗎?到時(shí)候請(qǐng)把我們的照片發(fā)給我。”我很驚訝,“啊?您會(huì)說中文啊!你們來自哪個(gè)國(guó)家?”“我們是英國(guó)人,我在上海工作。”我把我拍他們的本意告訴他,他說沒問題。我說我去過他們英國(guó)兩次,我家兒子早年就讀于巴斯大學(xué)。他高興地把這話告訴旁邊的女士。“您去過我們倫敦啊?”“我不只去了倫敦,去了巴斯,還去了牛津,劍橋,曼徹斯特,約克,多佛白崖,斯特拉特福德莎士比亞故鄉(xiāng)……好多地方呢。”他“哇”的一聲豎起大拇指。“這是我的家鄉(xiāng)。歡迎你們來鳳凰!希望我們鳳凰給你們帶來快樂!”加了微信,握了手。小伙子微信名叫“Ewan”,翻譯過來是“尤恩”,或是“伊萬”。
連夜整理了五張照片,第二天早晨發(fā)給了“Ewan”。他用中文回信息:“很有意思,我覺得這是一個(gè)很感興趣的事情。你拍得非常好!”文辭有點(diǎn)不通,意思我明白。其實(shí)談不上好,就是隨拍,自然,真實(shí),生動(dòng),他可能出于一種交際的禮貌。
從田興恕故居往道門口,在城隍廟弄口邊,老遠(yuǎn)看見兩個(gè)西方女士在“溫水魚療”館泡腳。看樣子她們走了很長(zhǎng)的路,選在這里休息,順便泡泡腳。坐在靠外的女士,發(fā)現(xiàn)我在拍她們,笑著用手做了“OK”,打了招呼,不上前問候顯得不禮貌,正好也可以近距離拍她們。我笑著走近,友好地問:“你們好!請(qǐng)問,你們會(huì)說中文嗎?”她們都搖頭,估計(jì)連我問什么內(nèi)容也不明白。只生硬地說三個(gè)音節(jié)“西——波——亞”,我明白了,該是西班牙人。我笑著點(diǎn)點(diǎn)頭,立馬想到,音樂是相通的,馬上哼起歌劇《卡門》里《斗牛士進(jìn)行曲》的交響樂版本,并用雙手打著節(jié)拍。兩位女士馬上興奮起來,一并“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大聲哼起來,也用雙手有節(jié)奏地打起拍子,全身隨著節(jié)拍扭動(dòng),全然不顧腳下盆子里抓咬他們腳掌的小魚兒。坐在對(duì)面的兩位年輕顧客和一旁的女老板開心地笑了,過往的游客紛紛駐足,圍著店面觀看。我口里一邊哼著,一邊舉起相機(jī),拍了她們快樂的樣子。
一對(duì)看似母女的外國(guó)人在“北京故事”店里選購(gòu)旗袍,姑娘長(zhǎng)得非常好看,很上鏡。店里貨架多,有縱深,不便拍照。女主人忙著照應(yīng)客人。我與男主人溝通,說明來意。男主人笑著說,店里本來不允許拍照,要拍的話,必須征得她們本人同意。姑娘正在試衣服,我與她“母親”溝通,她不會(huì)中文,說了一句話我也不懂。她打開手機(jī)翻譯軟件,用語音翻譯成文字給我看,她們是意大利人。我用同樣的方法,煞有介事地兩手展開,模仿著美聲,輕輕地唱:“啊多么輝煌,燦爛的陽光。暴風(fēng)雨過去后,天空多晴朗。清新的空氣,令人精神爽朗……”她笑著對(duì)我豎起大拇指,然后對(duì)著手機(jī)說,再給我看:“我的太陽。”我翹起大拇指,笑著點(diǎn)點(diǎn)頭,對(duì)著她的手機(jī)說:“您好!歡迎你們來鳳凰。您家閨女很美!我想拍幾張她試衣的照片,可以嗎?”她看后笑了,對(duì)著手機(jī)說幾句話,我一看“謝謝!她不是我女兒,是我侄女。你可以拍。”我說了“謝謝!”,做了“OK”的手形。她對(duì)正試著旗袍的侄女說了我的意思。侄女很爽快,認(rèn)真地試著旗袍,任由我拍照。可惜,場(chǎng)地有點(diǎn)窄,不便多角度多機(jī)位拍,不好構(gòu)圖,入鏡的物件也不好,勉強(qiáng)拍了幾張,不理想。
連續(xù)兩天,去聽濤山下沈先生墓地,在從文書屋,料想這世界文豪安眠而且很美的地方,洋人們會(huì)感興趣。不湊巧,沒有等到。工作人員譚雪很熱情,不厭我煩地反復(fù)展示茶藝。“可是怪了,前幾天就有幾波洋人來過,還給沈先生獻(xiàn)花,買了先生的書,還留下簽名的卡片。” 她打開手機(jī),給我看她拍攝的很多洋人拜謁先生墓地和購(gòu)書的照片和視頻,拍得很好。她安慰我:“不過總有來的,你安心等就是。碰不如等可靠。”樣子很肯定,很認(rèn)真。我信。
好幾個(gè)清晨,趕在旅游團(tuán)隊(duì)之前,來到北門碼頭,都遇見了洋人。他們對(duì)跳巖似乎很感興趣,估計(jì)他們那邊沒有,或是從來就沒有看過。一本正經(jīng)地看,膽戰(zhàn)心驚地過,樣子很好笑。鳳凰人男女老少像走平地一般,頑童們經(jīng)常在上面飛跑。
我在古城拍洋人,他們都很客氣,主動(dòng)朝我“哈嘍”,還要我把拍的給他們看,然后禮貌地“OK”!一對(duì)青年男女,以對(duì)岸吊腳樓為背景自拍合影,不滿意,邀請(qǐng)我?guī)兔ΑN耶?dāng)然樂意,拍過后,他們看了,非常滿意,翹起大拇指,連說“thank you”!
轉(zhuǎn)悠了好些天,拍了一些,沒有幾張很滿意的。心里顧慮,擔(dān)心被拍的洋人反感,甚至厭惡。不會(huì)講英語,不方便溝通交流。很多可能很好的人物和場(chǎng)景,不一定能遇上。
不過,這次拍攝,讓我感覺鳳凰離世界的距離越來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