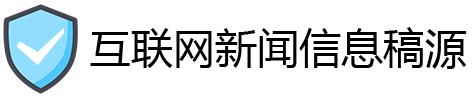彭武長
家鄉地處湘西大山深處,山多田少,巖溶干旱,主食以稻米出主,農耕完全靠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老百姓生產生活極為艱苦,吃不飽、穿不暖,生產隊沒有余糧喂養耕牛。寒冬臘月,草枯葉黃,牛放在山上吃不飽了,正好有稻草可以補充。為了不使稻草日曬雨淋,霉爛變質,讓耕牛有充足的食物來源,先人們就采用碼草樹的方法有效地存放稻草。碼草樹自然也就成了家鄉一項傳統的生產習俗。
家鄉的水稻一年只種一季,絕大部分種秈稻,但為了打糍粑和做小吃也會種一點糯谷。秋風起時,稻谷收割,用刷桶將谷子脫粒后,就將稻草扎成一把把小傘立在田里,若田里有水則將其拖到田埂上存放,曬十天半月,干透成金黃色,拿到手上一抖沙沙作響,就可以堆碼草樹了。
碼草樹要選好地方。在山寨東頭幾百米的牛欄邊,有一稍平緩的山坡,坡上的柏樹、樅樹高大挺拔,適合做草樹的軸柱,距山寨、牛欄及牛喝水的堰塘近,扯稻草方便,容易管理,是生產隊碼草樹的理想之地,草樹每年都會在此碼放。
糯谷草質較硬,牛吃不易消化,只適合打草鞋、搓繩索、鋪床鋪等,不適合做飼料。飼喂耕牛一般要用秈谷草。秈谷草和糯谷草要分樹碼放。
碼草樹不僅是力氣活,也是技術活。稻草曬干后,生產隊趁天晴就會集中勞力將田間的稻草收攏打捆背到草樹旁。草樹不是誰都能碼,碼的不好,東偏西歪,不緊實,扯稻草容易倒塌,特別是未碼成形,碼的不整齊,封頂未做好,容易受雨水侵蝕,霉爛變質。生產隊有幾位碼草樹的高手,我爹就是其中之一。每年一到碼草樹的時候,他們就會大顯身手。
首先要整理好地基。草樹底盤要平整,瀝水,若是坡地,要用樹木將其墊平,使其與樹干形成一個垂直的平臺。碼草樹一般是兩個人進行,一人遞草,一人碼草。根據碼草的數量決定草樹的直徑和高度,一般的草樹底座直徑一丈左右,高二丈左右。碼草時,要把稻草頭朝外,一個個稻草并排,一個疊壓著一個,稻草頭疊壓在稻草尾,草堆碼成圓形,一層層碼放。每碼兩層,要交錯放一圈稻草,將頭尾連接處壓平,并將稻草踩緊壓實,以防脫落。剛開始堆碼時,稻草外圈要碼整齊,再慢慢向外擴張。到了一定高度,遞草人只能拋草,碼草人接草,一拋一接,一擺一踩,如行云流冰,十分順溜。當稻草碼到一半高,就開始慢慢地收攏,使其形成錐形,再往上等稻草拋不上去了,遞草人就用木叉把草遞給碼草人,最后將一個較大的稻草分開似傘一樣固定在樹桿上,像給草樹披上一件雨衣。碼好的草樹成紡錘形,遇上雨雪天氣,雨水就會順著草樹邊緣流淌,對里面稻草不會產生影響,存放一年也不會變質。
碼草樹時節,也最適宜小孩們玩耍打鬧。那時鄉村沒有什么娛樂設施,大人碼草樹,我們或在旁邊追逐嬉戲,或把稻草胡亂地鋪在地上,打滾、打抱腰、翻跟頭、扎草人、捆掃把等,有時還會穿草衣跳毛古斯舞,雖會給大人們做工添些亂,但一般都不會受到責怪,只是提醒我們不能互相打架,注意安全。
上初中后,學校放秋收假,我曾幾次參加過生產隊碼草樹的勞動,當然只是背運稻草和給碼草人遞稻草。有兩次我同爹分在一個組,他碼草,我遞草。我想試著學學碼草,卻被爹一口拒絕。他說:“碼草別看簡單,是蠢門頭,其實也講究。你現還小,既不懂碼草章法,又沒有大的力氣把草踩緊,是碼不得草樹的,等你高中畢業回來耍牛屁股(務農)時,我會很好地教你碼草樹。”遺憾的是,高中畢業后回家務農一年多,有半年時間被大隊抽調到農建團去外村修水利,一年時間當大隊拖拉機手,無緣學到碼草樹的技藝。
草樹是耕牛的糧倉。我初高中讀書放假,生產隊安排我協助守了兩個假期的牛,爹當守牛員時,我也替他守過多次牛,對于給牛過草是比較熟悉的。凡到冬季,雖每天都將牛趕上山放牧但牛吃不飽,特別有的牛白天犁田、耕板土、拖木、拖碾等勞作,晚上更要補草。每次把牛趕到堰塘喝足水趕回牛欄后,就要在草樹上扯些稻草,撒些淡鹽水,掛在牛欄方上,讓牛享受稻草的美味。若遇冰雪天氣不能放牧或遇母牛產仔,就要將稻草剁成一節一節的,加上一些鹽水同煮熟的包谷或黃豆拌和,用大盆盛到牛欄邊,牛便會探出頭來,把嘴伸進盆里,一邊大口大口地吃食,一邊快樂地搖著尾巴,以示對主人的感激。
草樹是山里人不可或缺的生產生活資料。那時家鄉十分貧窮,缺衣穿、缺被蓋是常態。我家兄弟姊妹多,一到冬天饑寒交迫十分難熬,爹就會帶著我,跑到草樹上扯下幾大捆稻草,換掉床板上早已碎爛潮濕長滿跳蚤的稻草。晚上躺在重新鋪墊散發出清香的酥軟的稻草上,盡管身上只蓋著薄薄的爛棉被,也不覺得冷。正如汪曾祺先生在《冬天》中所寫:“床上拆了帳子,鋪了稻草……稻草裝在一個布套里,粗布的,和床一般大。鋪了稻草,暄騰騰的,暖和,而且有稻草的香味,使人有幸福感。”雖家里沒有粗布將稻草裝在套里,但同樣是暄騰騰的,暖和,既暖了身,更暖了心。稻草除鋪床外,打草鞋是主要的原料,燒灶也是很好的引火柴,曬草煙時夾煙的繩主要是稻草搓的,晚上外出也經常會抱一抱稻草用于照明,稻草渣也是燒草木灰或漚堆肥的好材料。
草樹也是孩童們的樂園。家鄉的山寨依山而建,活動場地很少,草樹也就成了我和小伙伴經常光顧的地方。每當放學后,幾個小伙伴不約而同圍繞著草樹玩耍,“抓特務”“捉迷藏”“過家家”,比跳躍,比爬樹,輸者學豬叫、狗吠、雞鳴、牛喊,一陣陣歡聲笑語在田野、山林里回蕩,大家玩得不亦樂乎。
最刺激的莫過于在草樹下套麻雀、套斑雞。冬天鳥兒在野外食物難覓,草樹就成了它們常去的地方。特別是麻雀、斑雞一群一群地飛到草樹下尋找稻草上殘存的谷粒,這就給我和小伙伴提供了套雀的好機會。放學后,我們提上下套的器材,在草樹下,架上竹篩,篩子上壓上硬木板,用小木棍將竹篩的一端支起約一尺高,篩子內外撒些食物做誘餌,把麻繩一頭捆在木棍上,另一頭拉到十幾米外的隱敞處,待麻雀或斑雞覓食鉆進篩中,用力將麻繩一拉,小木棍支撐的竹篩倒塌,覓食的麻雀、斑雞便被罩在篩子里了。
草樹是擋風避雨的溫暖港灣。山寨的草樹位于幾個村寨通往山外的大路邊,過路人一旦遇上刮風下雨,都會選擇在草樹下歇腳、躲雨、抽煙、扯談。記得有個初冬的傍晚,我同另兩個小伙伴吃過晚飯去草樹邊玩。走近草樹旁一看,有兩個穿著破爛的花邊衣,戴著小籮筐大頭帕的老太婆蜷縮在草樹下。我們一問得知,她們是外地因災歉收出來乞討,看天黑了便借草樹過夜,大半天沒吃東西了。我們看她們十分可憐,便跑回家告訴俺娘。俺娘說:“在家千般好,出門萬事難。她們未遇大難是不會出門討飯的,對于落難的人,要盡力幫助。”俺娘把家里剩的一碗滾豆飯、兩個蒿子粑、幾個蒸紅苕裝進飯簍,還端了半升子包谷米和一大缸井水,帶我和小伙伴到草樹下送給她們。她們十分感動,躬身致謝。俺娘的言行給我和小伙伴上了生動的一課。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家鄉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村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糧食實現了自給有余,每家每戶都碼了草樹,分到各家各戶的耕牛都有了足夠的草料。上世紀九十年代后,家鄉青壯年外出務工越來越多,飼養耕牛越來越少,耕田犁地多用農業機械替代,草樹也就十分罕見了。現在,每當下鄉偶爾看到一棵草樹,心情會十分激動,濃濃的鄉愁油然而生。那承載著鄉親們汗水與希望,守護著村寨的安寧與幸福的草樹,總在心中以一種無聲的力量,激勵著我善作善為,不負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