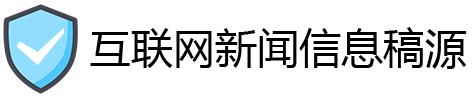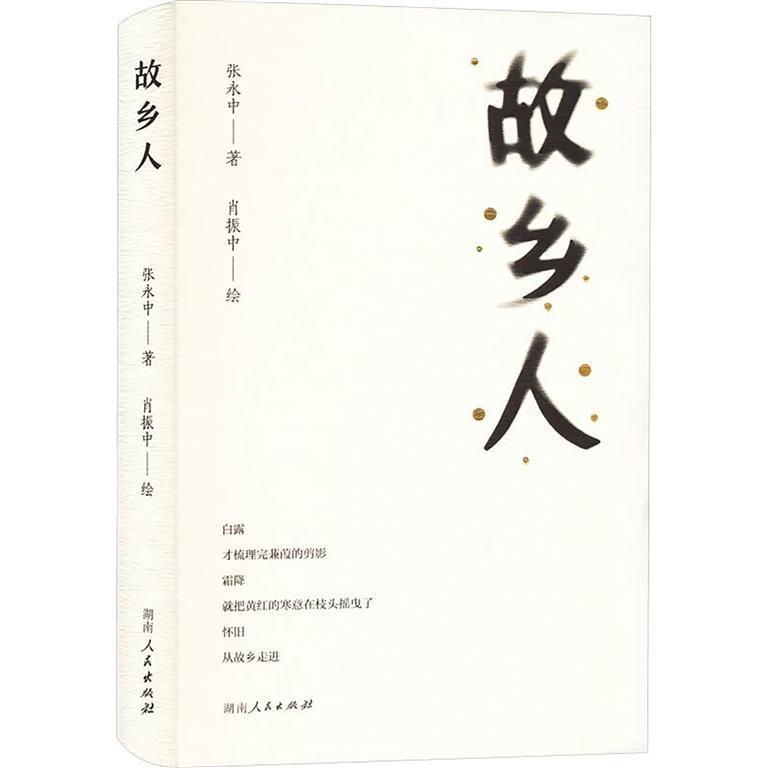
作者:張永中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4年1月
歐陽文章
張永中先生的文化隨筆集《故鄉(xiāng)人》不到15萬字,選入的文章也就21篇,應(yīng)該說是一本小書。王躍文先生卻稱他讀到的是一本“大書”,這當(dāng)然是有道理的。
《故鄉(xiāng)人》是一本有關(guān)湘西故土記憶的散文隨筆。一個在外奔波半生的“游子”,在歷經(jīng)了從縣域到州府再到省城的摸爬滾打后,于知命之年,從鋼筋混凝土包裹的城市中,深情地回望故鄉(xiāng),于是,故鄉(xiāng)的芭茅花、蠶豆、葛根、鳥窩……故鄉(xiāng)的阿婆、阿大、九舅、三舅……還有羅依溪的舊事以及舊時同學(xué)的悲慘命運……這些陳年往事被一一激活。在當(dāng)下的散文寫作中,這類回望故鄉(xiāng)的作品并不少見,《故鄉(xiāng)人》自有他的獨到之處。《有奶奶在的世界》《嫁在河蓬的阿大》里,爺爺、奶奶和阿大一生看似平靜,卻隱約可以感受到特殊歷史時期,批斗、劃分階級成分這些時代洪流在他們身上留下的烙印。《那年秋日》《芭茅花》里,我和同學(xué)應(yīng)錫的求學(xué)之路,表面上看,寫的是高考制度恢復(fù)后,鄉(xiāng)村讀書人的不同命運,從深層次看,更表現(xiàn)了社會制度的變化,對鄉(xiāng)土世界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和人心思想的深刻影響。《故鄉(xiāng)茶思》里,九舅的茶味哲學(xué)雖然經(jīng)久未變,但傳統(tǒng)的茶葉耕作和經(jīng)營模式卻隨著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
細加分析,《故鄉(xiāng)人》對故鄉(xiāng)的人事過往看似波瀾不驚的敘述中,蘊藏的是湘西鄉(xiāng)土社會的巨大變遷。《故鄉(xiāng)人》的獨到之處正在于:作者的寫作不只是在撿拾那些過往的“陳芝麻、爛谷子”,也不止于咀嚼那些源于親人生死命運的“喜樂悲苦”,他的寫作更隱含了時代發(fā)展下湘西鄉(xiāng)土社會的“蝶變”。比如,在《羅依溪記年》這篇隨筆中,作者在舅舅家過年,原本是歡樂的場面,作者卻突然發(fā)出“我們終究沒有在自己家里過年”的感傷,進而幡然自問:“我在哪兒呢?我的家在哪兒呢?我沒有了立于故鄉(xiāng)土地之上的房子,也沒有可以設(shè)案祭祖的神龕了……”作者內(nèi)心疼痛的呼喊,本質(zhì)上書寫的是我們在這個時代城鄉(xiāng)巨變中失去故鄉(xiāng)失去根脈后生發(fā)的“大陣痛”。這樣來看《故鄉(xiāng)人》,它更是一本書寫我們這個時代的“大書”。
受到特殊地理環(huán)境和神秘文化作用的影響,湘西的鄉(xiāng)土文化有著其迷人的特質(zhì)。百年前,沈從文以一個“鄉(xiāng)下人”的姿態(tài),進行浪漫化的鄉(xiāng)土?xí)鴮懀谩哆叧恰贰堕L河》《湘行散記》等一系列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構(gòu)筑了一個令世人向往的“湘西世界”。沈從文以降,鄉(xiāng)土文學(xué)一直是湘西作家創(chuàng)作的一條主脈。當(dāng)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湘西。當(dāng)下的湘西和沈從文所處時代的湘西已然有了很大變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dāng)下,快速推進的城鎮(zhèn)化進程、日新月異的科技發(fā)展、波云詭譎的世界政局等,都將深刻影響鄉(xiāng)土社會的倫理關(guān)系和道德秩序。同樣,湘西鄉(xiāng)土社會也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交織與裂變當(dāng)中。湘西作家對他們所處時代湘西的書寫從未停歇。我們熟知的蔡測海以“三川半”作為其文學(xué)意義上的故鄉(xiāng),創(chuàng)作出《地方》《家園萬歲》等長篇小說。于懷岸從“貓莊”出發(fā),寫出長篇小說《貓莊史》《巫師簡史》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說。黃青松以“花橋”為背景,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畢茲卡族譜》。一代代湘西作家試圖用自己筆下的“故鄉(xiāng)”來構(gòu)建“湘西世界”的當(dāng)下圖景。
從這個大的背景來看《故鄉(xiāng)人》便會發(fā)現(xiàn),作者筆下的故鄉(xiāng)——亮坨,其實就是他的精神原鄉(xiāng),是他鄉(xiāng)土寫作的原點,他把曾經(jīng)發(fā)生在故鄉(xiāng)亮坨的往事一一喚醒,其實更是借這個村莊人事的悲歡離合,來窺探湘西鄉(xiāng)土世界的內(nèi)在密碼,來展現(xiàn)一個時代鄉(xiāng)村社會的真實樣貌。所以說,“亮坨”,是無數(shù)中國村莊的一個,更是當(dāng)下湘西鄉(xiāng)土社會的一個縮影。正如王躍文先生所說:“無數(shù)亮坨構(gòu)成中華萬水千山,無數(shù)亮坨人構(gòu)成世世代代中國人。因此,亮坨很小,亮坨也很大。”當(dāng)然,在我看來,在《故鄉(xiāng)人》中開啟的“亮坨”敘事才剛剛開始,“亮坨”還有待更深入的挖掘,“亮坨”可以更大,作者對湘西鄉(xiāng)土世界的書寫還有更廣闊的空間。
《故鄉(xiāng)人》在散文寫作風(fēng)格上亦有其特別之處。從語言上,作者用純正的故鄉(xiāng)語言來書寫故鄉(xiāng)人事,鄉(xiāng)音俚語,就如故鄉(xiāng)的芭茅花、野果子、山泉水,帶著一種純真的山野氣。就如龔曙光先生在序言中寫到的:“有一種撲面的野趣。”張永中曾從事多年的沈從文著作的編輯工作,大概因為“近朱者赤”的原因,他的筆調(diào)中又帶著沈從文散文“拙樸雋永”的意味。“野趣”和“拙樸”結(jié)合到一起,《故鄉(xiāng)人》里的文字顯得更有“生趣”。《那年秋日》里,作者高考失利,心情不好,炊煙不再“裊裊”,而是“癱軟在瓦脊上”。《有泉在山》里,行走在山路上,遇到山泉,“再順山打一聲哦嚯,真是神仙也不換的愜意。”《山路》里,寫春天,“山醒了,是被各種鳥雀吵醒的。”這些充滿著山野氣息的語言,充融著豐沛的想象,展現(xiàn)出語言的創(chuàng)造性和強大的生命力,這樣的語言無疑是好散文的稟賦。
好散文難寫,特別是書寫文化題材類的散文。如果文史材料用得過多,易成“文史體”。只停留在所見所聞,又會陷入“文旅體”。過于高高在上、裝腔作勢,一不小心成了“說教體”。太注重辭藻的流暢和結(jié)構(gòu)邏輯的穩(wěn)當(dāng),不覺間成了“作協(xié)體”。總體而言,《故鄉(xiāng)人》很好地規(guī)避了這些散文寫作上的“窠臼”。值得一提的是,張永中多次強調(diào),他是“界外人”,他從來沒有把自己當(dāng)作一個專業(yè)作家在進行寫作。我想,正是這種從容、放松的狀態(tài),讓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脫離了規(guī)規(guī)矩矩,讓他手中的筆更為靈動自由,讓他的文字更為“生趣”也更有“活力”。特別是作者做過高校學(xué)報編輯,當(dāng)過行政領(lǐng)導(dǎo),多個崗位上豐富的人生閱歷,開拓了他的視野,豁達了他心胸,這樣,當(dāng)他再回眸故土的時候,更能“跳出湘西寫湘西”,更能看清楚湘西鄉(xiāng)土世界的本質(zhì)與必然。從而,他對故鄉(xiāng)的書寫所顯露出來的格局和境界也就更為寬廣。
當(dāng)然,寫作不必去遵循或模仿某一種風(fēng)格,千姿百態(tài)、百花齊放,才是文學(xué)應(yīng)有的樣子。但是,寫作自有高低。真正的好散文應(yīng)該有真誠的寫作態(tài)度,應(yīng)該遵循大道至簡的規(guī)律,應(yīng)該有充融的文學(xué)性和創(chuàng)造力,應(yīng)該張揚生命的獨特體驗,應(yīng)該傳達對世界的深刻認知……對每一位寫作者而言,本質(zhì)上,缺少生命的焠練,便永遠無法寫出生命的真諦。
我想,《故鄉(xiāng)人》僅僅只是張永中書寫文學(xué)湘西夢的一個開始。湘西,還有一本更大的書,等待他,等待更多的寫作者去書寫。